2025-04-05 11:34:47照明科技園
暮色將血與塵土渲染成瑰色時,她跪在破碎的神龕前。十指插入凹凸不平的石縫,指甲劈裂的聲響夾雜著遠處此起彼伏的哀嚎。綱手抿了口苦澀的藥水,喉管里翻涌著青草藥液和鐵銹的味道——這具臭烘烘的軀殼,連呼吸都是罪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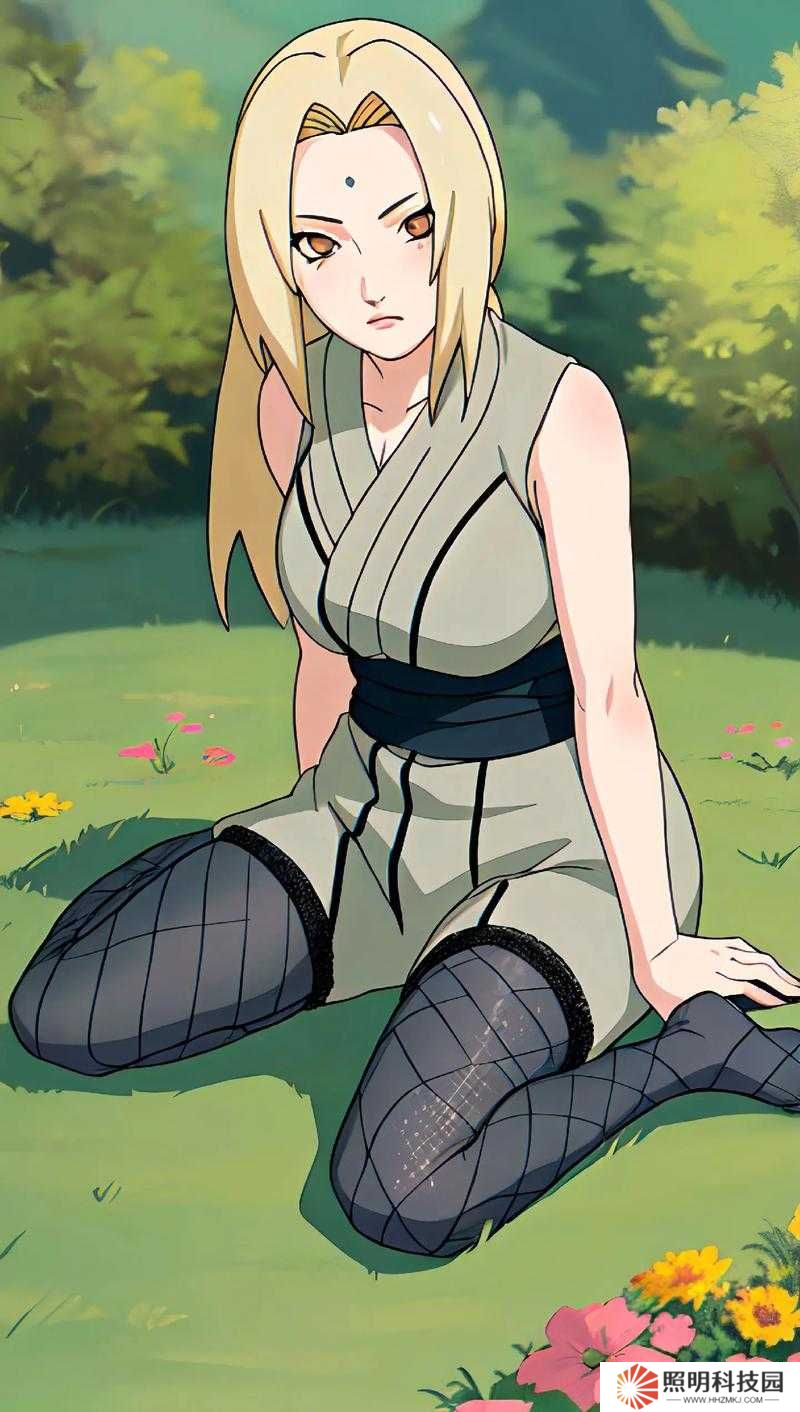 一、醫者手中埋著掘墓人的骨
一、醫者手中埋著掘墓人的骨蛇叔說她命里有條逆水行舟的河,擱淺在爛泥里算不得死。這瘋話倒貼著些理,畢竟活人怎會想著刨活人的皮。可戰場上的手術刀終究抵不過螺旋狀的醫書,當紅蓮教徒的利刃剖開戰袍時,她手里攥著的還是一把解剖刀。
"你手里的血都是半生緣。"老神棍攥著沾滿骰子的肥手這么說。她嗤笑一聲擲回茶盞:"半生緣?滾蛋!"茶水潑在油燈上,騰起一簇青煙。
二、紗布裹著整座城邦黑曜石鑄就的教堂頂上積著枯骨,麻雀啄食白森森的指節。綱手攀著裂開的尖頂往上爬,裙擺被風撕成血腥色的旗。石階第三十八階暗嵌著彈簧機關,她早記得——去年那支奉藏**就是在這臺階被她揉碎的。
"你到底是該死的瘋醫,還是該活的圣手?"冷槍從絞刑架后探出槍口。她扯著嘴角笑:"神總愛問這種蠢問題。"
三、血脈在手術臺下暗涌消毒水把所有溫熱都揮發干凈了。橡膠手**在砂紙般的骨節上,她執刀的手指微顫——不是戰栗,是十年沒碰刀具的生疏。但當動脈涌出血柱濺在護目鏡上時,那個徹夜趴在尸體堆里解剖的姑娘回來了。
床頭擺著做舊的懷表,指針卡在三刻十八分。那是他們第一次掰開十字鎬亂戳時的鐘點,像極了夏日午后從溫室里滾出來的蜥蜴。綱手摸著后頸發涼的傷疤,那里還殘留著三天前軍醫打的縫合釘。
四、最后的復蘇液月光把戰壕照成銀色的祭壇。她跪在傷兵身邊剝他燒焦的皮肉,指甲縫里卡著焦糊的碎骨。這時遠處傳來戰鼓聲——不是硝煙里的昏聵,而是某種宿命的吆喝。
"疼不疼?"她問那軍人。"比你的吻溫柔多了。"綱手嗆著碘酒笑了。這盛世狂歡,倒頭來還是血肉鋪就的床褥最溫柔。
五、多余的第四針解剖刀劃開掌心紋路時,暗紅的符文滲出鐵銹味的血。那是十五歲時叛逆著在血管里灌的墨汁,說是要刻骨銘心,后來才發現那是印著某人名字的幽魂符。
槍管抵著背脊骨時她忽然想起,六年前他也是這么霸道地捏碎她的鎮痛劑。說來好笑,這亂世里的愛情果然是暴力美學,就像手術臺旁的拷問床——都要把人剝離成**的骨架。
六、遠比死亡更漫長的等待戰事像污濁的潮水退去后,醫院只剩空蕩蕩的白墻。消毒柜里還躺著那把青銅手術刀,刀鞘上蝕著兩人錯雜的指紋。她裹著白大褂癱在椅子里打盹,夢見自己又化身三十年前那個暴躁女學生。
窗外桑椹樹綴滿紫黑色的果,像極了某種未愈合的傷。綱手掰開手指數著樹影,這才驚覺自己居然還活著——或者說,終于又到了該赴死的時刻。
笛聲從廣場飄來,混著遠處火刑架的焦糊味。她站起身拉平大褂褶皺,活像要去給誰主持最后一場手術。暮色在腰間凝成帶血的繭,那些年割過多少人,就結多少個痂。
夜霧里傳來槍聲,伴著某種類似金屬碰撞的脆響。綱手推開門診室的門,這次倒不著急摸手術刀了——反正命不該絕的人,總要撐到自己的白旗降下。
聲明:本文內容及配圖由入駐作者撰寫或者入駐合作網站授權轉載。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,不代表本站立場。文章及其配圖僅供學習分享之

新品榜/熱門榜